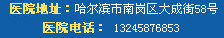北京治疗白癜风最有效医院 https://jbk.39.net/yiyuanzaixian/bjzkbdfyy/mbbdf_zx/emwsafw/在文人的眼里,处处都是诗,酒更是诗。刘醒龙去了一趟二郎镇,就看到,“树已微醺,石也微醺。微醺的还有那泉,那水,那云,那雾”。当然,这些意象都很清醒,微醺的是作家的心灵。没错,酒,就是诗。中国的情形不必赘言,在古代,几乎每一句诗都是从酒坛子里捞出来的。在西方,古典希腊,诗人与酒神狄俄尼索斯关系密切,诗的迷狂性,正是酒的性格。北欧在文明上比较落后,从原始社会直接迈入资本主义社会,但关于酒与诗的关系,他们的神话最具代表性。在北欧神话里,奥丁(漫威电影里雷神的父亲)是无上之神,地位相当于古希腊神话中的宙斯,而他同时也是北欧神话里的酒神。他从巨人的女儿手上骗来了一坛仙酒,一口气喝光,变成一只鹰飞回诸神的居所阿斯加德,巨人也变成一只鹰穷追不舍。诸神见奥丁飞回来,拿了一只桶,让他把仙酒吐出来。他吐出来的仙酒,催生了人类文学史上所有伟大的诗人。因此,酒的重要作用,就是产生诗。然而,酒,又不仅仅是诗。它更是人对庸常生活的反对,诗只是其中一种反对方式。试以青花郎为例,解此谜团。宇宙中心作家朱文颖到了二郎镇,听到郎酒人说:“中国人总是要喝酒的。”这是一句真理,但还不够普遍。更普遍的说法来自美国国父富兰克林,他说“人天生就是要喝酒的”。他认为,除了人类,没有任何动物可以如此优雅地喝酒。而人类能优雅地喝酒,得益于生物结构,我们是直立着的,并且肘关节的位置恰到好处,让手能够拿起酒杯,刚好送到嘴边。如果不能直立,显然谈不上优雅;如果肘关节位置太靠前,则酒杯够不到嘴唇;反之,位置太靠后,则会把酒杯伸到脖子后面去。富兰克林是个新教徒,他相信生物结构是上帝的设计,因此,人能优雅地饮酒,“证明上帝爱人,并且愿意看到人类幸福”。饮酒,就是顺从上帝,圣子告诉后人,圣餐上必须有葡萄酒。而对中国人来说,饮酒,就是“道”的要求。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对真理,重点在于自圆其说。现在富兰克林已经解决了人们饮酒的合法性,并且赋予了它神圣性。接下来的问题就是:怎么获得酒?酒不仅仅是诗,逻辑由此展开。贾平凹来了,从成都到二郎镇,花了足足8个小时。他这才知道,“二郎镇就在大山深处”。在那个建筑在赤水河畔陡峭的山坡之上的小镇里,一个老头问他是否来自北京,并且说北京虽好,“就是太偏远”。“老头的话说得好啊,站在这里,北京是偏远的,上海是偏远的,所有地方都是偏远的。”在这个二郎镇老头的心里,二郎镇就是宇宙的中心,就是“阿斯加德”。然而老头显然知道北京、上海,并非“不知有汉,无论魏晋”,他把二郎镇认作宇宙中心不是出自无知。赤水河南岸的二郎镇老头不是个人中心主义者,这个中心不是他,而是青花郎。青花郎就在二郎镇,离它的故乡越远,自然就越偏远。反过来看,其实是二郎镇实在太偏远。高山深壑,地无三尺平,自来人烟稀少,生活维艰。但,它却出产中国最好的酒。天赋有两个常识是既定的,一是酒来自粮食,二是有人才有酒。前者是农业问题,我们不可能饿着肚子酿酒;后者是商业问题,美酒来自市场激励。要解释清楚青花郎的来时路,就要真诚地面对这两个常识。先来面对第一个。前现代的中国历史,是饥饿的历史。中原千里沃野,江南鱼米之乡,匮乏尚且是常态,何况赤水河畔这连粮食都很难长出来的穷山僻壤?因而我们看到,郎酒的前身,是西汉的枸酱——一种用苦涩的野果拐枣酿成的酒。它与粮食无关,所以合情合理。当地人天生酿酒的禀赋,硬是把无用之物转化为连汉武帝都“甘美之”的好酒。无法不把它归结于天赋,因为人类学证据还不能提供其他更有说服力的解释。女诗人葛水平说,二郎镇上“那终年萦绕不散的老糟味道……便是郎酒散发出来的香奈儿五号”,这里所指向的其实就是天赋。如果你看过电影《香水》,也会相信香水的萃制来自天赋。天赋酿造枸酱,但枸酱不足以令人止步。一种东西越是匮乏,人们就会越是想望。匮乏与想望的时间足够长,想望甚至会变成一种来自遗传系统的饥渴。《人类简史》的作者赫尔利就说,人类有“贪吃基因”,喜欢最甜、最油的食物;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仑说,长颅金发的白人喜欢草地,因为他们的先祖是游牧民族。经验也告诉我们,经济承受能力越弱的人,买肉的时候越偏向肥肉;过去数十年里,浓香型白酒一枝独秀,也是因为酒对中国人而言太稀缺了,而浓香型“酒味”最浓。这种遗传性的饥渴,让最匮乏的粮食酒,成为历史上最令人想望的酒——这一点,对青花郎的诞生至为关键。智慧的先民将要找到解决之道了——用最难吃的粮食来酿酒。米红粱“连猪都不吃”,与生存问题不冲突;而它生命力强,可以在穷山僻壤里茁壮成活;并且,它的硬,是因为它的支链淀粉含量高,酿造酱香美酒,偏偏非它莫属。用最不好吃的粮食,酿造出最美的酒,这也是中国人的天赋。第二个常识,有人才有酒,人多酒才好,解释起来就简单多了。其实贾平凹已经注意到,赤水河畔生存环境恶劣,历来人烟稀少,但从清朝开始,盐业运输的兴起,为这里塑造了一个完整的社会结构,也为当地出产的酒通向更广阔的市场创造了交通条件。万事俱备。平静的美酒作家张炜评述二郎镇时说:“航道,战争,美酒,这三样事物加在一起,就不再是寂寞边地了。”这三者的确是在二郎滩上纠缠在一起的。航道与美酒的关系,就是市场、交通与物产的关系,前面已经说清楚了。而他说的“战争”,指的是红军四渡赤水——这可能也是阎连科把二郎镇无处不在的酱香味形容为“一股深红的味道”的原因吧。这一场战争的作用,是让郎酒扬名,而与它的形成无关。事实上,美酒之诞生与延续,恰恰因为它远离战争与政治,恰恰是得益于既连通了市场却又仍然是“寂寞边地”的环境。美酒来自粮食,粮食对古代社会,意味着安定。战乱之时,无心也无力酿酒。而二郎镇远离政治中心,也使得中国历史上频繁颁布的禁酒令难以对它进行有效约束,从而保持了美酒工艺和生产的稳定性。郎酒两河口生态酿酒区也就是说,美酒的背景,应当是平静的。女诗人傅天琳写郎酒,一开头就在思考:“要是能在大城市酿造就好了。”这是一种现代浪漫主义,社会生活的剧烈变迁,让诗歌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就逐步迁居到城市里去了。城市意味着原料、市场、能源、科技、劳动力,以及生产和运输的效率,诗人的想法合情合理。不过,美酒酿造向来都是一种农业,生产上有强韧的地域性,生产过程也秉承着经验主义、精耕细作的农业传统,产量可以扩大,但产程无法缩短。青花郎是平静的生命过程的结晶,正如“在大地上绣花”的中国经验主义农业。它的诞生过程被概括为“生长养藏”四步曲,每一步,都是宁静的生命和内心演化过程。一年的酿造周期,至少七年的基酒储存老熟时间,以及数十年的老酒参与勾调,这会让效率至上的现代工业望而却步。现代世界是喧哗的,正如人们饮酒时的躁动与热烈,但酒的生产本身,却是平静的、缓慢的。“它不是和时间比快,比的是慢。”这是作家魏微了解过郎酒的生成历程之后发出的慨叹,而她的确攫住了美酒生成过程的核心特点。她是在天宝洞里发出如此叹息的。每一个造访二郎镇的名士,都会被天宝洞深深震撼。天设地造的储酒溶洞,兵马俑一般陈列的酒坛,数十上百年的时光历练,人与自然各司其职的天人合一作工,必定会直击所有初到者的心灵。因为它引导着人们回到终极问题——我们和天地之间到底存在何种关联。作家李琦说,天宝洞对郎酒而言,是“无可复制的神来之笔”,她在其中,感受到一种哲学意味和宗教体验。作家娜夜则说,“天宝洞对郎酒来说,是众妙之门”。天宝洞哲学、宗教、众妙之门……的确如此。如果把它补充完整,这个排列应该是这样的:科学、哲学、宗教、众妙之门。科学是现代生活的依据,但今天的科学虽然昌明,对于大千宇宙而言,仍然只是夜空里的星光,所能照亮的区域非常有限。那些科学所未及的领域,对人类而言一样重要,我们无法忍受它的一片混沌,所以要借助哲学、宗教,来作出可接受的解释。而哲学、宗教并不意味着迷茫,多数情况下,它转化为人的浪漫主义情怀,让我们对善与美始终心怀向往,人反而因之变得透彻了。就像面对青花郎,身临其境,你就不得不接受它的出现相当程度上是一种自然恩赐这一结论。而面对恩赐,人们必定会本能地给予一种善意的回应。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现代中国,这个小镇上的人们始终能保持一种单纯的赤子之心。那些酿酒的匠人们虽然没有宗教,却对自己的事业始终贯彻着一种自发的、宗教般的虔诚,他们由此越发地清楚自己在做什么。“众妙之门”,是“玄之又玄”,只可描述,不可定义,这就是“道”。魏晋玄学,把玄解释为“无”,佛家的参与,让哲学变得更缥缈无形,但却产生了一种出尘脱俗的美。把天宝洞比作“众妙之门”,是恰当的,在那样一个空间里,我们可能看不到什么神奇的实相,但在酒坛子里,神奇的转化一直在发生。也不是完全不存在神奇的实相,酒坛子上覆盖着的厚厚酒苔,便是洞中特有,今日也尚未得到科学解释的。作家苏童进去摸了两次,“第二次的触觉几乎令我震惊,我所触摸的,很像是酒的皮肤”。“你怎么能想到呢?酒是有皮肤的。”这是他的心理活动,他并没有因为震惊而喊叫。进入天宝洞,人们都会自觉地安静下来,它自身那种旷古的宁静,是一种直透心灵的强制力。其实,这一力量在二郎镇无处不在,人与自然之间,确立了一种独特的伦理契约,它不在纸面上可见,但却在心灵上可感。因此敏感的诗人雷平阳才会这样写二郎镇:“……爹一样的山,妈一样的河,哥一样的树,姐一样的雾,妹一样的清风,弟弟一样的石头……每一幢房子旁边,就长着姑妈一样的青草,姑姑一样的菜苗……”来到这里的,还有两位大作家——莫言和余华。这两个人的共同点,就是都不懂酒,不懂酒的人面对酒反而更可爱。余华说,在天宝洞,“我觉得我懂酒了”。为什么懂了?因为酒与哲学关联起来了,而作家具备对哲学的敏感。莫言也一样,他从天宝洞出来之后仰天一叹:“这样的好东西,当用一种庄严的心态去细细品尝,狂喝滥饮,无异于暴殄天物。”这让人想起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,他对《二泉映月》的评价是:这样的音乐,应该跪着听。余华更有趣,想起这些年看到的一些人,嚎叫着把名贵的白酒和红酒像啤酒一样干杯,愤然说:“这些人应该去喝假酒。”这会让人想起周星驰在电影《少林足球》里的一句话:“球,并不是这样踢的。”嗯,酒,并不是这样喝的。应该怎样喝呢?更美的生活中国美酒是世界上最好的酒,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生活也是世界上最精致的生活。然而我们必须承认一点——在过去,饮用美酒、精致的生活,范围非常有限。数千年历史上,匮乏是社会基本面,生存是大多数中国人面对的根本问题。即便在汉唐盛世、康乾盛世,饥饿也依旧触目惊心,而饥饿导致的粗糙的生存方式,是多数人不可逃避的处境。正因如此,那场和二郎滩紧密相关的“四渡赤水”的战争,才在历史上具有特别的意义,因为它帮助我们走向了一个新的中国。新中国最大的功绩,是结束了战争,解决了饥饿问题,并且引领着十几亿——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庞大数量的中国人,走向富裕,走向现代化。横向比较,我们仍需谦逊,但如果和中国自有文字以来的历史进行纵向对比,当下的时代毫无疑问是历史上最好的时代。全面消灭饥饿,接近全面消除绝对贫困,这是在过去的历史上从未达到过的。这就意味着,美酒具备了被全民共享的社会条件,精致的生活也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成为现实。正因如此,面对青花郎这样的美酒,我们就应该有小泽征尔那样的庄严,应该郑重地去正视莫言和余华的愤激:酒,不是这样喝的。强大的消费能力召唤了对美酒的巨大需求,大市场带来的价值转换,支持了美酒的产能扩张,科技进步让美酒的勾调、包装与分发都更加高效。这意味着,今天,或者不远的将来,美酒可以抵达每一个中国人。就像作家阿来面对郎酒庄园的“千忆回香谷”那71个巨罐时的有感而发:“只要挣得到酒钱,这辈子好酒是饮之不尽的。”然而,怎样饮用好酒,是当下我们亟需补上的一堂课。三五赤膊汉,一瓶陈年酒,几只钢化杯,数口乃见底——这不是青花郎这样的美酒应有的归宿。美酒,不是作家刘元胜所形容的“带点香味的辣水”,它隐藏着一座通向彼岸的桥梁。饮酒,是为了以物达意,借助酒的催化作用,通向我们的精神。而所谓精神,是指在日常生活中无法获得的超越性体验,体验文化,体验情感,归根到底是体验美。审美,是人与万物的区别,所以饮酒的终极价值,是让人感受到人本身的意义。生活可能繁琐而疲累,与动物的觅食没有根本区别,审美在其中遍寻不见,但一杯美酒,就会让我们超脱生活,超脱动物性,回到美,回到人。正如朱文颖在郎酒留下的思考:“喝酒的人,唯独不见现实中的自己。”作家熊召政去过二郎镇后,发出了一个令人会心一笑的提问:“如果地球上每个国家都是盛世,你愿意生活在哪个国度?”当然,答案还是中国,因为中国美酒。“世界上没有一个酒厂可以仿制出茅台和郎酒。”倘若能够以物达意,就不会辜负美酒,不会辜负盛世。作者
李淳风统筹
张鹏霞排版
GINNY南风窗新媒体出品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abmjc.com/zcmbzz/9088.html